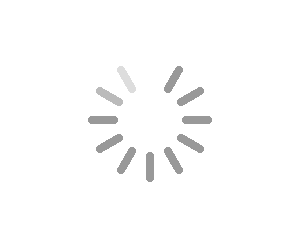防空洞分为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两大类:公共防空洞供普通市民使用,也被称为市民洞;私人防空洞包括专供机关团体职工及其家属使用的机关洞和专供家庭使用的个人洞,洞内设施状况差别极为悬殊。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作者:周翔
1943:一个断面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沙啦啦拉上铁门。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
这是张爱玲1943年发表在上海《天地》杂志第二期的小说中的片段,勾勒出彼时上海街头最突如其来又最常见的景象:封锁。虽是小说,城市的镜像在其中却质感真实,触手可及。非常态的“封锁”之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骤然打断,被抽离而出的人们则试图向这决策的执行者徒劳地要求继续他们的日常:回家买菜做饭,去一趟医院,或者去工作。
这种小范围、短时间的封锁时常发生,而战争后期对上海市内较大威力的封锁发生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在租界最繁华的南京路、浙江路一带。上海的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孤岛见闻》一书中写道:“封锁地区周围布置了沙包、铁刺等障碍物,断绝了交通,只留下几道缺口由日本宪兵把守。封锁线内市民所需柴米菜蔬和日用品等等,都被断绝供应。幸而日本宪兵不久就撤退了,改由巡捕接替,而巡捕是可以‘讲斤头’的,只要给以一定的好处,不但货畅其流,人也可以偷进偷出。”表面上的相安无事,背地里的暗流涌动、缺口百出,越来越成为上海的常态。
在日军已经全面占领上海的1943年,日军统治下的秩序看似井然:推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集合若干保为一区,被选中义务担任保长职位的中国人不得推诿;18岁到30岁的男子,要加入“自警团”,由各区各保甲做好名册,每一个团员要轮值站岗,维护当地的治安,严防反日活动。这种“以华治华”的政策,一方面出于日军维护上海安定局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由于在越来越长的战线中他们开始变得分身乏术。“每个团员都预备一根粗绳,只要警笛一响,或是有什么暴乱情况,自警团就采取行动,用绳子把这个区域四周围住,从此人车都不得通过,交通即刻断绝。与此同时,他们要用电话通知警局或军事当局,片刻之间,警车或者军车抵达,就在这四条绳的中间挨户搜查。”当时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在他的书中写道。然而大多数时候这些措施并不很有效果,何况人人“都有家务或职业,谁有工夫常做自警团呢”。于是出现了专门替人站岗的职业,只要能花钱请“替身”,大都能躲懒。虽然白花了冤枉钱,到底日军的统治也“可见一斑”。
战争已经逐渐进入第七个年头。“从日军占领租界以后,1942、1943年我们就能感觉到慢慢的各方面统治反而松一些,只是原来在租界里面的一些有钱人受到打击,老百姓没有什么变化。”老上海刘复田说。1934年出生的他在战时上海度过了童年,幸运地在战乱以及此后政权更迭的年代里,一年不落地读完了中小学。但这似乎并不是特别值得惊讶的事情。“尽管政权交替,只要你按部就班地念上来,上学完全不受影响。教材可能会变,教学仍然继续,顶多中间停几天课,除非你自己中间想去参加革命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正常生活的中断是个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离开上海的,大都是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或者左翼的文化界人士,市民阶层、通俗小说作家很少走,他们虽不走,但很少听到有落水与日本人合作的,日本人也不太管他们。”
陈子善的父亲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因公职去了内地,经昆明再到重庆,母亲则留在上海,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与他的父亲汇合。当时的上海市面,陈存仁、刘复田的回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日本宪兵要求路过关卡的人们都要脱帽、俯身行礼,否则极容易被军棍、皮鞭抽打。
同样,“在北方的农村,抗日武装和日军一直是对峙状态、剑拔弩张的,但在北平、上海情况就不太一样。新的统治者都需要维持表面的繁荣,除非自己选择离开,日本人并不会把你赶走。1937年刚开始打仗时,上海人支援抗战情绪高昂,战争进入常态后,就变成一种消极的抵抗——平常过日子,沉默的大多数。好多人没有走,还留下来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文学家唐弢曾回忆,抗战爆发后,流出了大量旧书,卖得很便宜,他就不断地收集,大量“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藏书由此积累而来。而当时郑振铎也在上海居住,收集元刻本、明刻本等珍贵古籍,不仅出于私人的行为,还代表中央图书馆等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他还注意到,1943年有一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是汪伪政权收回了租界。之所以能够做到,大背景是轴心国从1942年开始战局吃紧,尤其是当年11月同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以后,日军希望汪伪政权宣布参战,以壮声势。1942年12月,汪精卫访日,日本方面提出请他宣布正式参战。回国之后,汪精卫发布了参战的三个条件,即“收回各地租界”、“统一华北政权”与“恢复国旗原状”。1943年1月,日本宣布“退返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意大利和当时主政法国的维希政权也随后声明放弃上海以外的在华租界。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最晚收回的,直到1943年7月31日,汪伪政权与法国签署协议,完成了“收回租界”的目标。对于这一事件,陶菊隐曾写道:“两租界交还后,上海市民所感到不同的,只是各机关的屋顶上改挂了国民党的旗子,巡捕的帽子上改佩了绘有国民党旗的新帽徽,服装和面孔还是老样子,除越籍巡捕解职而外,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那些收买路钱的家伙。”
租界的收回对于仍处战时的上海市民生活并无太多实际影响,也未使上海城市格局产生太大变化,但这一日军在沪统治政策的调整,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1942年以来战争形势的变化。差不多同一时期,1943年8月23日,日军结束了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长达5年的轰炸,此前1942年日军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轰炸重庆市区。这也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兵力部署发生了重大调整,大批军事力量被牵制,重庆的制空权基本被中方在美方的协助之下掌握。
在重庆大量挖掘防空洞的措施,此时倒“转移”到了上海,因为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日军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还要每家门前掘一个6尺深的防空洞。“当时上海有名的女画家周炼霞1944年发表了一首她填的词《庆清平·寒月》,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般人都以为这是情诗,其实她写的是空袭时候的上海。友人来家里谈天时遇到空袭警报一响,只能关了灯对坐,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陈子善说。
那时节,上海只有清一色的“伪报”,市民不能从当地的报纸中获取真实的信息。“所有的新闻,都是一面倒的日军‘胜利’的消息,但市民读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对每段消息,都从反面来推测。”陈存仁写道,日军对上海实行越来越严苛的经济统制政策,煤荒、米荒、油荒,限用电量日益减少。“马路上的街灯也减少了,所有商店的霓虹灯全部停用,整个市面成为黑暗世界。因此,一般市民都认为越是黑暗得早,越是象征天快要亮了。”